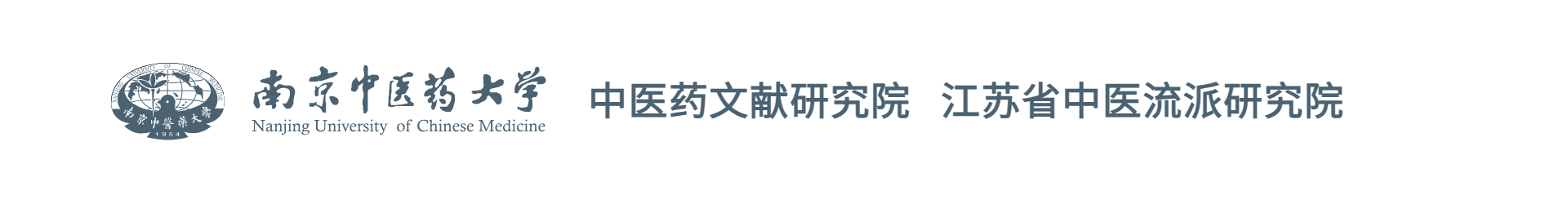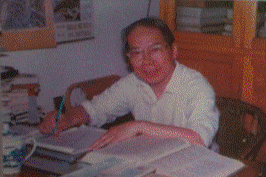
江苏吴江市人,著名中医学家、中医药文献学家,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自幼从父习医。1956年8月于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伤寒论》教学、中医药文献研究和临床工作。历任江苏省中医学校伤寒教研组副组长、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组副组长,南京中医学院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江苏省重点学科中医药文献学科带头人。兼任南京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中医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南京市第九、第十届人大代表、江苏省中医学会中药研究会委员、《江苏中医杂志》常委、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文献学分会常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等。主持编写《中药大辞典》《伤寒论释义》《中药学百科辞典》等工具书和教材8部,以及参加编写《诸病源候论校释》等8种古医籍,校注《伤寒准绳》《温疫萃言》等古籍。发表论文几十篇。由宋立人研究员领衔总编的《中华本草》是一部划时代、立丰碑、集大成的本草巨著,被誉之为当代的《本草纲目》。临床擅治内科杂病,尤其对消化系统疾病、血液病及肾病的治疗经验丰富,效果显著。
成长经历
宋立人家学渊源,学有根柢。其家六世业医,祖寅伯先生精儿科。父亲宋爱人先生为江苏名医,对伤寒、杂病造诣精深,名声享誉苏浙北一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中央国医馆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和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温病教研组组长,为江苏省中医教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宋立人在世医家庭的熏陶下,自幼即立志从事济世救人之业。宋立人6岁入学,同时父亲又先后聘请了徐儆予、陆子丹二位宿儒作家庭教师,专门教授古文,为他后来从事中医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4岁那年在教会学校——乐群中学读书的同时,即开始随父学医,继承家学。宋爱人教授不仅医术精湛,而且教学有方,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学问皆由精思博览而来,然基础之学要以多诵熟读为始,多诵不在乎涉猎浮夸,而在乎精专一致,朝夕不辍,数载行之,不独熟能生巧,并且神参化境。”提倡要“学有系统,古今贯彻”“稽古而上及素灵,取新而下及近代。”在父亲的指点下,宋立人从《内经》《难经》入手系统学习了中医学基础理论和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尤以伤寒和温病学著作,用功最勤。习医6年,前四年读书、侍诊,后二年到苏州阊门外一慈善机构的诊所担任诊疗工作。在该诊所,病种较多,是难得的临证锻炼机会。他悉心诊疗,书写病案皆效父亲之法,证、脉、理、法毕备,处方选药,十分审慎。夜间灯下枕上,对日间诊治病例,皆反复思考,揣摩再三,遇有疑问,或请教父亲,或就问师兄,或查阅书本,直至弄清疑问,确立好下一步治疗方案。
“纸上得来终觉浅”,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方可得到真知灼见。因此1947年春季,怀抱济世救人之心的青年宋立人,毅然离开苏州城,回原籍吴江同里镇独立开业,开始了自己的医学生涯。开诊之初,困难重重,遇到疑难病证,再无师友指点。他奋发图强,潜心学习,细心探索,终于使诊疗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宋立人深有体会地说:“临证之初,往往有两点难以掌握,必需予以重视:一是审因辨证,尤以病因复杂、虚实互见的病证,更易使人疑虑不定,难以措手;二是要熟练掌握药物性能和应用规律,这些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提高。”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中医药文献研究和教学工作,但他始终没有中断过临床医疗活动。在临床工作中,他对于调治脾肾尤有心得,曾系统进行“以补脾法治疗慢性肾炎”的临床研究,对脾胃病、血液病的治疗有丰富的经验与显著的临床疗效。
临证思想
一、辨证辨病结合,提高医疗水平
在临床医疗方面十分重视辨证与辨病的结合,认为中医从来就是重视辨病的。宋立人指出必须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与辨病论治相结合。辨证是辨病的进一步深化,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病人的不同个性。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医疗的特色,其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科学的合理内核,应该继续提高,使之更加完善。同一种疾病由于证候有差异,甚至寒热相反,虚实互异,如果见病治病,势难万全,辨证不明,死生立见,正确的治疗既要治病,还必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根据疾病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机体反应,对证处方。
二、 生命之本,系在脾肾
宋老认为肾脏不仅具有促进生长发育,生殖繁衍,生髓化血等功能,而且肾所主宰的先天元气是推动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又是真阴真阳的基础,在转化和调节人体的重要功能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脾主为胃行其津液,是气血资生之源,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和调于五脏,都要依赖于脾的输化功能,始得营养全身。更重要的是脾主后天之气,其中尤以宗气的作用为要,它主持气血升降出纳,统摄营卫流行,调节脏腑机能,并对人体起到温养护卫作用。先后天之气是互相依存,互相为根的,脾之运化水谷,依赖于肾阳的温化作用,肾之元气,要有脾脏为之转输水谷精微,两者对维护人体之正常功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宋立人提出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以脾肾相结合的核心,充养脏腑,调节功能活动,为人体生命之本。所以在治病中十分重视对脾肾的调治。
脾胃虚损,气血精微不足,其它脏腑失去滋养之源,常会导致疾病,而其它脏腑的慢性虚弱性疾病,久延不愈,也多涉及脾胃,这时脾胃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往往成为一个决定转归的关键性脏腑。所以在临床尤注重理脾胃阴阳、协调脾胃升降、权衡脾胃虚实。
补肾必须遵循阴阳互根的准则。宋老认为调治肾病,补益肾元,必须重视阴阳互根这一规律,采用“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治法,既不失主次之分,又具有互济之功。所以宋立人在补肾中十分推崇张景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治法。
杂病久延,可致肾虚。宋老认为肾是人体水火之宅,阴阳之本,关系到生命源泉的一个脏腑,病及于肾,根本受损,所以治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有时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关键,医者于此,切不可掉以轻心。基于肾虚证候,多由久病传变而来,因此同一肾虚证候,由于其原有疾病不同,所表现的具体症状也就不尽相同,其治疗用药也应有区别,应该按照病、证、症结合的方法,作出更加切合病情的治疗措施。
老年病是老年期所特有的一组慢性病,宋老主张补肾为先,但以平补缓收其功,忌峻补急功近利。若求补心切,擅用滋腻峻补,或于病有碍,或虚不受补,或阴阳失衡,故治老年病补肾,即便病发之时,若补肾阳,非阳虚沉寒,不用温燥辛热,如附、桂之属;若补肾阴,非阴虚火旺,多忌滋腻降火,如熟地、知、柏之流,常效景岳阴阳互根,水火互济之法,补肾阳方中寄补肾阴之物,补肾阴剂中存补肾阳之品,就药物组成而言,总是补阴补阳同在,惟是剂量侧重而已。
学术思想
一、对《伤寒论》的研究
宋老研究《伤寒论》主张从源到流。认为《内经》《难经》及《神农本草经》等医典,是中医药学之根本,万法之宗源。他说:学习《伤寒论》,如果不读《内经》《难经》,就难明阴阳之理与脏腑气血经络之关系,也就难以真正认识《伤寒论》一书所论病证之性质,病位之所在,病情之寒热,邪正之胜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能否学好用好《伤寒论》,取决于对《内经》《难经》《本草经》等经典著作研究的深度。
(一)对《伤寒论》的认识:
《伤寒论》问世以来,深受广大医家的重视,被奉为医门之圭臬,至今仍作为中医院校的必修课。但对《伤寒论》的看法历来不一。自晋、隋、唐迄宋、明、清,中外注家如林,竟达四百余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其说。宋研究员对这一问题,有独到之见,切中肯綮。
1、主论风寒,兼及温热。
宋研究员研究《伤寒论》不拘前人之见,更不妄下断言,而是注重实事求是,他认为《伤寒论》并不包罗万象,论治百病,所论述的只是部分外感性疾病。就《伤寒论》整个篇幅来看,是详于风寒,略于温热。对中风、伤寒之六经传递,证因脉治的变化,论述非常详尽,相比之下,其于温热各条则只有提纲,既未论其传变,也未详立方治。
2、六经论伤寒、八纲统百病。
《伤寒论》以六经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将伤寒发病及其传变过程中的各种不同证候,与六经所属脏腑的病理变化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八纲是外感病和内伤杂病的辨证总纲,《伤寒论》虽无八纲之名,而有八纲之实,在六经辨证中包涵着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宋研究员认为,《伤寒论》确实论述一些杂病证治,这是由于伤寒发病过程中每有杂病相并发。或先有内伤杂病,然后再感伤寒;或先有外感风寒,然后又犯内伤;还有一种是由外感病误治所致的坏证。所以仲景在系统论述伤寒时必然要论及部分杂病。不然就不能详尽地叙述伤寒病的发展变化。另外通过伤寒与杂病的证例,正可以提高临床辨证思维能力。所以宋老特别强调,不能因此而认为《伤寒论》就是伤寒与杂病合论之书,否则不仅模糊了《伤寒论》以伤寒命名的本意,甚至在辨证方面会导致既不能认清伤寒,也不能辨别各种杂病的错误结果。宋立人进一步指出,后世医家采用类法、类证、类方、类症的手段来研究《伤寒论》,以反映辨证论治精神,有其可取之处,但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伤寒论》。经过他们重新编次组合之后,已不能反映伤寒疾病发生发展之规律。
3、六经证治重在阳明、少阴。
六经统领三阴三阳。太阳病是表证,阳明病是里、热、实证,少阳病为半表半里证,三阴病多属里、虚、寒证。三阳病以祛邪为要,三阴病以扶正为主。宋老深察六经病之缓急主次,提出六经证治关键在于阳明与少阴两经的观点,认为阳明病是伤寒外感病邪热亢盛之极期,其病最甚,而少阴病是正气衰弱之竭期,其病最危,都是临床治疗的关键,这是由阳明与少阴本身的生理、病理特点所决定的。他认为后天之阴阳盛于阳明,先天之阴阳充于少阴,为人身生命之所系。阳明是六经病邪之出路,为病最烈,常经一清、一下而病愈,但又往往暗藏杀机,如治疗不当,正不胜邪,必致危殆。少阴为六经之根本,病最危急,常关系到生命的存亡。阳明与少阴是六经病证治之关键,应该十分重视。
(二)主张寒温统一,发展仲景学说:
伤寒与温病是外感疾病的两大类,其根本的不同点在于感受邪气不同。叶天士、吴鞠通一直被作为温病学派的代表,但宋立人却说,叶、吴是真正的伤寒大家,是学、用《伤寒论》之佼佼者。并且指出,研究《伤寒论》的最高境界是寒温一统,而不应该是寒温之争,应彻底摒弃世俗之偏见,创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医外感病学。
二、本草文献的研究
(一)本草研究思想
1、综合性本草是本草学研究的主体:综合性本草是指载药范围广,涉及药物各个专业内容的本草著作。是各个时期药物知识的总结。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是我国本草书中的代表性著作,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本草学的主要成就及其发展水平,因此,宋立人认为研究综合性本草是研究本草学的必由途径和基础。并且指出在历代综合性本草中,当以宋代《证类本草》为首要著作。因此宋立人对《类证本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深入开展专题性本草的系统研究: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深深地体会到,要充分挖掘古代本草著作的精华,还应开展专题性的本草学术研究,他将专题本草分食疗、炮制、民间药物、中药药理、临床应用等等,都很有研究的价值,应该得到重视。
3、考订品种,发掘民间药物:民间药物是本草中药物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本草如《本草拾遗》《日华子本草》记载了较多的民间药都被收载于宋本草中,扩充了药物种类。宋老对《本草纲目拾遗》曾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考证工作,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经过周密的查证,对有争议的几十种药物基源得以确定。为后人学习研究该书,扫除了障碍,为提高《本草纲目拾遗》的实用价值、发掘民间药物,充实现代本草学内容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4、探索方书的本草内容,总结药物临床应用:宋老认为古代医籍方书中蕴藏着大量的本草资料,因其与临床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药性功用的记载往往早于本草著作,是研究药物的另一个广阔领域。因此,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本草,就必须重视对方书中有关本草知识的探索。他着重研究了《小品方》一书,利用方书中的药物学内容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我国的本草学。
5、研讨日本学者的本草:宋老认为日本为我国一衣带水之邻邦,文化交流从来就很密切,日本学者一方面把中医药传回其祖国,同时在他们的应用与研究中,又不断获得新知,为发展中医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出现了很多颇有价值的医药方书,如《质问本草》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要全面研究本草学,也不能忽视对东邻学者著作的研究。
(二)新一代本草学的实践
1、编纂新时代本草著作,是历史赋予的使命:宋老自从60年代编纂《中药大辞典》以后,继续系统研究历代本草文献,发掘历代本草的宝贵遗产,认为《中药大辞典》做了不少整理工作,但是限于当时条件,不仅广度深度不够,而且没有系统阐述我国本草学的学术体系。所以他很早就蕴酿着编纂一部综合性本草专著,以此作为自己整理研究本草文献的奋斗目标。数十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在本草文献、中药普查、中药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的研究,以及医药等方面均取得大量成果,使条件和时机逐渐成熟,因此,在1986年卫生部中医司“中医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座谈会”上,他投标“《中华本草》的研究和编纂”这一科研课题,经反复论证而中标。
宋立人研究员指出,开展《中华本草》的研究和编纂工作,必须以继承发扬、整理提高为宗旨,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既要总结传统药学,重视民族医药,又要反应现代中药的科研成就。在学术上突出医药结合,融会古今,在体系上突出传统本草的特色,因此要求旁搜博采,集古今本草之大成,发煌古义,融会新知,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充分体现全、新、精的特色,使本书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先进性、实践性和权威性,成为一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划时代本草巨著。
2、新时代本草著作当确立新的本草体系:《中华本草》是篇幅浩繁,容量较大的本草学著作,为了既具备本草的传统特色,又体现当代的中药发展水平,指出首先必须在上述指导思想下,依据本草学的学科领域和内在规律按照中药各分支学科的内容特点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建立一个新的本草体系。这一体系的实现,主要体现在药物分类系统和总体框架的设计,以及项目设置、体例安排等方面,为使8000种药物,严密系统有条不紊地依次叙述,历代本草都将药物分类作为确立本草体系的首要任务。纵观历代本草,药物分类的改进,正是本草学向前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所以他对《中华本草》的药物分类曾作了深入探索。他主张《中华本草》的药物分类,应该引进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遵循自然属性,采用现代的矿、植、动物分类系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年来他通过对本草的研究和编写实践,以及在李时珍分类法“类”下设“族”的启示下,认为由于当今药物之大量增加,分类层次只到科属为止是不够的。某些药物较多的“属”,必须进一步分组,才能适应当前分类编排的需要。如防己科千金藤属,药物达20余种,如不作进一步分组,则仍然繁杂紊乱,科条不清。如再将各种无块根的千金藤和各种有硕大块根的地不容分列两组,则排序清晰,没有紊乱错杂之缺憾了。不仅药材的形态结构特征,判然区分,而且有利于对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功能主治进行相互类比和系统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揭示药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加强药物的系统性,在分类学上为《中华本草》建立一个新体系打下基础。这一系统的完成,又将进一步推动中药研究的进程。
宋老撮取诸家本草之长,融会古今药学于一体,在保持传统本草特色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本草》的总体设计。根据从源至流,从内到外,从基础到应用,从理论到实际的原则,将全书分为卷首,正文和附编三大部分。
卷首部分,除凡例、目录外,着重列出“历代本草序例”及“历代本草书目”“本草要籍解题”,首先展示本草学理论发展及其主要文献的基本面貌。
正文部分,列总论与各论。总论对本草学作出全面系统的总结性论述。要求以历史唯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以中医药基本理论为基础,总结本草学的传统经验和理论,以及现代的研究成果。分列“绪论”“本草发展史”和“本草学通论”三篇。其中尤以“本草学通论”为主体,系统论述中药品种、资源、栽培、药材鉴定、炮制、制剂和药性理论等内容。形成一个具有我国民族文化特色的现代本草学理论体系,使本草学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
药物的完整概念,应包括“名、物、性、用”四个方面,正名定物,是确立药物的实体,性能、应用,是药物功效的体现。综此四者,概括了药物的内在本质。《中华本草》各论部分药物项目的设置,正是为了揭示这些属于药物自身的内在本质。因此他从药物的名称(包括正名、异名和释名)、生药学知识(包括品种考证、植物形态、药材等),药物生产技术(栽培、采收、炮制、制剂)化学成分、药理等,最后到药物性能应用(药性、功效主治、应用与配伍、附方)等建立了23个项目,形成每一药物的系统。他通过药物分类、总论和药物项目三个系统,以容纳历代本草文献和各个分支学科的大容量药学知识,建立了新一代本草的学术体系。
3、整理研究历代本草文献是编纂新一代本草的基础:认真整理研究本草文献,从中汲取药物生产和临床应用的经验及其学术理论,是继承发扬传统药学遗产不可缺少的重要步骤,是进一步发展中药学的基础。
他认为编纂《中华本草》,必须站在文献学的角度整理本草文献。对文献的处理也有严格要求,如[炮制]、[药性]、[功能与主治]、[应用与配伍]、[集解]等项目,要求忠实地引用历代本草文献的原文,从而反映出学术上的源流和前后承继关系,这也是保持历代本草精华的特色之一。[药论]项,对诸家文献,既要精选又要严密组合,因此书中药论已不是古文献资料的堆砌,而是按不同的命题进行了整理归纳,重新编排,并设立标题,相同的命题、不同的论点编排在同一标题之下,从而使药论论点明确,一目了然,同时也加强了药论的实用性,真正体现药论的价值。
他指出值得重视的是《本草纲目》“集解”部分,是陶弘景以来历代本草学家通过调查考察、辨疑正误,研究本草的精华部分,不仅记载着药物形态鉴别、品种演变,而且还有产地栽培、采集加工、药学史料等内容,如果摒弃了这一部分,将使本草研究成为无本之木,失去了进一步发掘的源泉,有损于本草学术的继承与发扬。所以,编纂新一代本草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切实做好文献工作,在广泛收集文献的基础上,汲取精华,全面总结药物生产和医疗经验,系统整理学术理论,考订药物品种,澄清用药源流,才能真正做到集历代本草之大成,编成一部划时代的本草巨著。
4、新时代本草当注重医药结合,力求实用:中医中药是祖国医学遗产中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药学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和临床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药的应用与研究离不开中医理论的指导,中药理论的发展,应用范围的扩大,均依赖于中医临床实践。因此,医药结合,相辅相成,是历代综合性本草的一大特点。本草学不仅有生药学方面的知识,又详尽地记载药物的性味功效、临床应用和中医药学基础理论,而且后者在本草中占据很大比重。所以《中华本草》的编撰工作必须遵循这一要求,着重总结中医药理论和医疗经验,并且将这部分的重点放在临床应用、药性理论及附方三个方面:
宋立人研究员认为《中华本草》的编撰,还应满足临床医务人员和中医药科研工作者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中药发展的最新成果,揭示医药动态,因此,本书对现代中药、药理、化学成分、临床应用等方面新成果的收集整理尤为重视,完全反映与展示了古今中药发展的新动态和新水平。
教育学科
宋立人研究员于1956年8月开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对本校伤寒学科有开创之功,对中医文献学科有建业之绩,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重视学科建设,培养后继人才
从1956年留校,至1960年,宋老一直担任伤寒教研组副组长(宋爱人任组长),具体负责《伤寒论》教学工作。在缺乏借鉴的情况下,教研组全体成员在他的的带领下,硬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在编写教材、探索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一)深入钻研《伤寒论》,搞好教材建设:宋老认为教材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作为《伤寒论》教材,他组织教研组老师对有关《伤寒论》的主要学术问题和教学难点反复研讨,深入领会,并广泛收集资料,考察各家学说,以加深理解,主持编写了多种伤寒教材。其中《伤寒论释义》是全国各中医药院校中出版较早的教材之一,该教材增强了《伤寒论》教学的系统性,对于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进一步总结经验,不断整理充实,撰成《伤寒论教学参考资料》,以供教学和学习者参考之用。其初稿于1958年9月在北京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上展出之后,受到普遍关注,在很多兄弟院校要求下正式出版。此外,他还主编了为西医学习中医用的教材《伤寒论纲要》等。
(二)组织集体备课,提高教学质量:宋老认为在教学过程中,集体备课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这不仅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而且也是提高教研室总体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措施。作为这种集体备课成果之一的《伤寒论译释》,就是这样编写出来的。宋老为之拟订了编写计划,设计了体例。该书在保持宋本原貌的前提下,选集诸家学说,条分缕析,理论联系实际,不尚空谈,因而在内容上比教材更充实,范围也更广,且浅显易懂,对教学和研究都有参考之用。
(三)多学科教学,培养人才:曾先后为中医进修班、中医师资班、全国中医教研班等系统讲授《伤寒论》课程,并为南京市西学中班、朝鲜留学生以及1978年附属医院举办的中医提高班上过《伤寒论》课。由于密切结合临床实践,教学效果良好,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60~70年代,曾指导医疗系学生毕业实习、临床带教,70年代初,还曾担任《中医诊断学》教研组负责人,参与江苏五所医学院统一教材的编写工作,负责诊断学讲义的审修,并担任过一段时间中医诊断学的教学工作。80年代后他又率先提出招收中医药文献学研究生的计划,作为硕士和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培养了硕士研究生6名,博士研究生6名。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反映了他扎实而丰厚的中医药理论基础,也为中医药事业的教学作出了很大贡献。
二、建立中医药文献学科
南京中医学院的中医药文献研究工作始于50年代,宋立人研究员从60年起,一直是编写组负责人之一,至1979年,宋立人研究员负责起草了将原编写组改建为中医药文献研究室的报告,并得到批准,他任该室的副主任,1985年任主任,1986年中医药文献研究室扩建为中医药文献研究所,他又担任首任所长,为中医药文献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辛勤操劳,贡献良多。1960年,他转到《中药大辞典》编写组工作,任编写组副组长,从此开始了中医药文献的科《中药大辞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大型中药工具书,是对本世纪70年代以前中药各学科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
宋立人研究员又相继担任《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药学》的副主编、《中医大辞典·中药分册》《简明中医辞典》中药学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87年担任《中华本草》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总主编。多年的科研实践,形成了宋立人研究员以本草文献为基础,考订品种为重点,总结临床疗效为归宿,进行医药结合的多学科研究的本草学研究特色,取得的成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为国内本草学界所瞩目。这些不仅为学校赢得了荣誉,为学科建设奠定了文献研究基础。该学科经过40多年的发展,经宋立人研究员等一代前辈的不懈努力,已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级重点学科